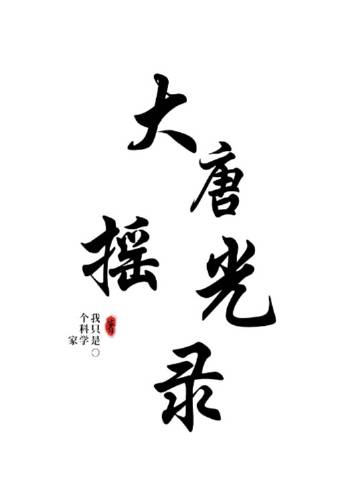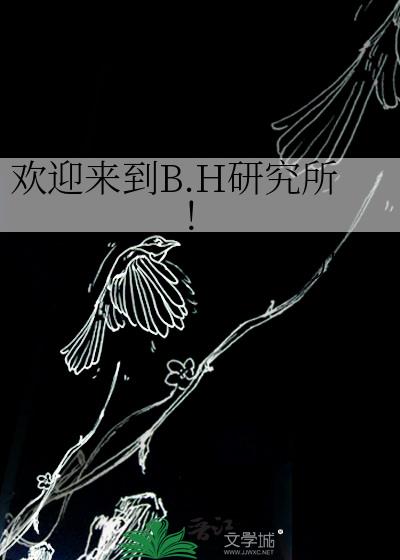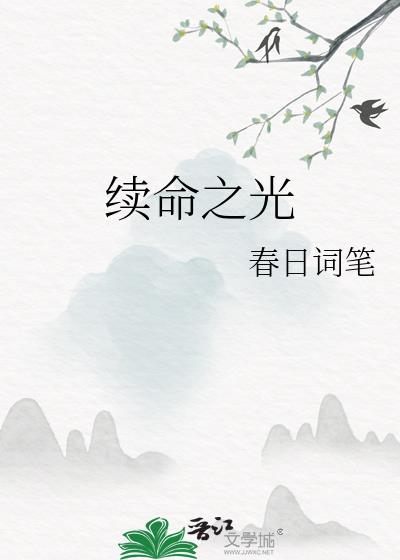鳴鶴(重生) — 第 39 章 猶折梅花帶雪歸(四)
第39章 猶折梅花帶雪歸(四)
風遲遲沒有來。
翃都軍苦苦支撐, 局勢越來越危險。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翃都僅剩的兩名副将一左一右站在顧珩身邊,相視一眼。
“将軍,無風, 便借人力!”
顧珩有些遲疑。
“再拖下去,戰損更是不知幾何!将軍,我們清楚手下的兵, 我們都是願意的。”
顧珩看着幾乎被血染紅的水面,沉默地點了點頭。
火船出發了。
沒有外力推動, 火船都等到十分靠近敵方戰船時才燃起。為了真正接觸到對方的大船, 除了用來點火的船只, 還有許多載着士兵以作幹擾的小船。
此策終于生效。
敵軍的大船由鐵索相連,一旦短時間內無法擺脫火船,便只能陷入火海。
火船上傳來蒼涼卻充滿殺伐之氣的尺八聲,在一片喊殺聲和嘯聲中, 顯得格外清晰。
總攻的時間到了。
時近黃昏,天際殘陽如血,濃重的紅光落在衆人眼中, 士兵們根本分不清夕陽亦或血光。
他們的四周是無邊的濤聲,濤聲的盡頭是在火中墜落的戰船。
血水共長天一色。
直到挂在水邊亭子檐角上的夕陽一縷一縷地收盡。
泷灣的一曲紅波,也漸次朦胧而平靜起來。
此戰, 大勝。
亦是慘勝。
沉淪多時的翃都終于迎來了今春的第一片火紅的霞光。
大戰過後,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立碑祭奠。
翃都衆人在泷灣邊擇了一塊傍山臨水的地,将所有将士的衣冠骨灰收在一處。
從守城的第一日, 到出城決戰的最後一個黃昏, 許多将士的屍骨皆尋不到了。
但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都被清晰地、一筆一劃地刻在一塊塊石碑上。
祭天這日, 顧珩帶着翃都剩餘的将領在墳前拜下,梅長君帶着那日遇見的小姑娘, 裴夕舟帶着城中許多自願入前線的百姓,還有所有墳中人的親友、街坊、每一個被他們守護的百姓,都跟在後頭浩浩蕩蕩地拜下。
泷灣熙熙攘攘,墳前寂靜無聲。
衆人極其沉默地做完了所有祭奠的事項,然後靜靜地看着碑前随風搖曳的火光。
一個略有些稚嫩的哭聲隐約響起。
這一聲仿佛是一個信號,讓許多壓抑的聲音有了釋放的出口。
哭聲一層蓋過一層。
泷灣大地上,回蕩着一曲低沉而哀切的挽歌。
天色漸漸陰沉起來。
在一片絢爛的日光中,突有濃雲壓境,細密的冷雨夾着雪花落下。
一個綁着繃帶的士兵望着天空:“是他們也哭出來了嗎?”
“是他們也哭出來了!”
百姓們紛紛擡頭,站在飄飛的冷雨中,嘴中呢喃不輕地呼喊着。
有幾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重重地點了點頭,滿是皺紋的臉上漫着一抹說不清道不明的笑意。
蒼老的聲音不大,顫顫巍巍地落在了衆人耳畔:“哭出來就好了……”
“哭出來……他們就能升天了。”
冷雨又細又密。
這是翃都的第一場春雨,半空中雪與雨相互交織,落在衆人身上便悄然融化。
在連天的濃雲中,日光始終不曾遠去,每一滴雨雪,都映着暖紅的光。
梅長君微微仰頭望向天際,有一絲冰涼的雨順着微紅的眼尾淌下。
……
戰事結束,百廢待興。
梅長君陪着顧尚書和顧珩在軍營整理江浙防務,言談間提起了江浙本地軍隊的弊端。
“除了少數的一些地方,江浙那些富庶城鎮的兵将們仍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顧珩看着各地呈上來的報告,搖頭道。
蠻夷終于被打退,江浙卻并非一派欣欣向榮。
改稻為桑的政策弊病開始顯現,各地殘亂的軍隊同樣也是不小的問題。
“父親,當時您手下那些江浙的軍隊,究竟是何等模樣?”顧珩望着顧尚書,有些好奇地問道。
“有一部分,”顧尚書閉了閉目,“在作戰之前,總是要求知道敵方的人數,然後自行商議,如果認為打不過,直接裝死不戰。”
顧珩嘴角扯了扯。
“還有一部分,比較聽從指令,無論敵方多強,他們也不會拒絕,而且在紮營築城之類的安排上,他們認真負責,從無怨言。”
顧尚書回憶起最初的幾場戰役,神色沉凝:“到了戰場上,如果敵軍撤退了,他們會主動請求追擊。”
“這不是很好嗎?”
梅長君聽在耳中,看着顧尚書一副頭疼的表情,有些疑惑。
“單單這些确實挺好,但最要緊的是……”顧尚書壓了壓自己的太陽穴,呼出一口氣道,“如果敵軍進攻,他們就會迅速撤退。”
“當然,如果敵軍再退,他們又會去追,但如果敵人卷土重來,他們會立即撤退。”
“如此循環往複,直到真正短兵相接之時,他們會果斷放棄。”
然後留顧尚書和身邊親衛在戰場上,震驚地看着他們飛奔而去的背影。
“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顧尚書無奈地笑了笑。
“刀子沒有落在自己頭上,他們又怎會放棄維系許久的‘原則’……此次蠻夷受了重創,短時間內不會卷土重來。但只要他們仍然存在一日,江浙就仍有戰亂再起的風險。”
顧珩附和地颔首,放下手中毛筆,同樣沉嘆一聲。
“陛下不會放任許多兵力留在江浙的,等亂子一平息,我們這些援兵又會盡數調走,江浙境內剩下的,又是那些極度圓滑,甚至未經受戰火的充數殘兵。”
梅長君若有所思地道:“既如此,必須讓江浙的兵将們自己立起來。”
她看了看軍營外翃都将領們的身影,笑道:“有了這次戰火的洗禮,翃都軍中,倒是有許多優秀的将領堪當此任。”
顧尚書接過顧珩遞過來的戰績和名單,一邊勾畫着名字,一邊點頭。
“翃都軍确實不錯,有血性,有機敏,但這人數……”
“這正是我要向您提議的事。”
梅長君從袖中取出一個早已備好的折子。
“我與國師此前有過商議,江浙軍隊的弊病在于人心,富庶之地,人心思穩,一時難以改變。”
“但江浙可用之兵不只有他們……”
她含笑輕聲講述自己在義烏的所見所聞。
顧尚書細細聽完,眼眸一亮,就要派人将折子遞與京都。
這折子是梅長君同裴夕舟在這幾日不斷修改而成的。兩人熟悉朝務,對當今陛下的心思也頗為了解,是以這個經過數次改進的文書,在顧尚書老練的目光下,已是極為妥善。
“極好,極好!”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勇!”
顧尚書捋着胡須朗笑出聲。
“諸如義烏等地之人,彪勇橫霸,善戰無畏,破文海廢文都在企鵝裙思尓二而吾酒一寺企,更新若在類似之處征兵,再輔以妥當的訓練,蠻夷之亂必平!”
……
翃都,上元夜。
戰火已矣,城中明燈三千。
皎皎明月高懸,在熱鬧的城中灑下一片靜谧的銀光。
百姓們的生活漸漸回到了往昔。
人群熙熙攘攘,漫步走在街上的梅長君眉眼微彎,望着燈山的方向,思緒漸漸有些飄忽。
“長君。”
一道溫潤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她回過頭,發現裴夕舟已悄然走至她身旁,眸中是一抹淡淡的笑意。
“一起看燈?”
她點點頭。
兩人随着人流往前方走去。
天邊最後一縷晚霞淡去,濃重的夜色漸漸襲來。
賞燈的人群不減反增,人潮如織,摩肩接踵。
在百姓熱情的推搡中,梅長君身形一晃。
“小心。”
他隔着衣袖牽了過來。
梅長君側眸望去。
上元佳節,他一襲白袍立于燈火之畔,眸色融融,牽着她的動作帶着幾分小心翼翼。
她晃了晃神。
沒有掙紮。
兩人就這般緩緩行至一座燈山下。
此處位置較偏,來往行人不多,在夜色中蘊出一份朦胧的靜。
四下無聲,只有盈盈火色在風雪中漾出暖光。
“長君。”
裴夕舟停下腳步,松開牽着她的手,從袖中緩緩取出一個精致小巧的簪盒。
“先前說的年禮……戰事結束的這些天,總算如約做好了。”
他将簪盒遞了出去,溫潤的聲音暗藏了些許緊張。
梅長君轉身看了過來。
恰好對上了他一雙如墨的眸,專注、溫柔,甚至帶上了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虔誠。
心中有些莫名的情緒在升騰,她定了定神,淺笑着伸出手接過簪盒。
“是夕舟自己刻的?”
“嗯,不知花樣合不合你的喜好。”
梅長君緩緩将簪盒打開。
那種莫名的情緒随着動作漸漸濃烈起來。
她輕輕拾起玉簪,視線朝簪頭那朵栩栩如生的梅花落去。
這一瞬間,街上的行人與嘈雜的聲響沒了。
面前暖意融融火色鮮明的燈山也沒了。
她站在翃都上元夜的燈會中,望着記憶極深近乎刻入骨髓的玉簪花樣,怔怔出神。
心中有個聲音轟然響起——他為何知道這個由她親自設計的花樣?
無論是花瓣的層疊,葉脈的方向,還是正中央那個,在她前世一次醉酒後,于圖紙上畫出的精巧卻有一筆差錯的符文。
所有的細節,分毫不差……
梅長君擡眸向裴夕舟望去,只見在燈山火色的襯托下,眼前人的輪廓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
她想起刑場那日,他一身素衣跪在雪中,清峻風骨同前世墓前一模一樣。
她想起觀南寺中,他擱着素帕為她擦去指尖香灰,低頭時眸中神色複雜如暗夜深湖。
她想起從京都趕往江浙的路上,他極為自然地喚她“夫人”,想起他一些沒有緣由的轉變,以及除夕醉酒,折梅相贈時他令人有些不明所以的話。
原來如此。
不是故人相逢少年時,而是故人,魂兮歸來。